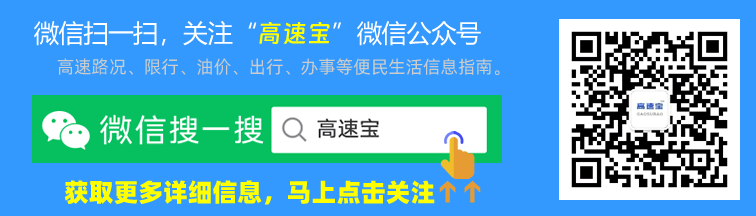放“夏”烦恼,卸“夏”疲惫
立夏了,人们照例要说一些“快乐安康”的吉利话。我向来不很信这些,但也不愿扫了旁人的兴,便也随众附和几句。横竖话是空的,声音是散的,一出口便随风飘去,杳无踪迹了。

春确乎是去了。那春日的花,春日的草,春日的蜂蝶,都随着春的挥手而隐去。人们每每感春伤春,其实春何尝因人的感伤而驻足?它自来自去,与人无干。而今夏来了,人们又忙不迭地要与它相守,仿佛夏是什么可亲的物事。夏之可畏,人尽皆知,却偏要装作欢喜的模样,这大约便是人的世故罢。
放“夏”烦恼,卸“夏”疲惫,说来轻巧。烦恼岂是能随意放下的?它们如同夏日里的蚊蚋,嗡嗡营营地绕着人转,任你如何挥手驱赶,总不肯轻易离去。而疲惫更是渗入骨髓,如影随形。人们白日里汗流浃背地劳作,夜里又在闷热中辗转反侧,这般的疲惫,如何卸得下?
街角的老槐树下,常见一个赤膊的汉子。他日日在那里摆个小摊,卖些时令瓜果。太阳毒辣辣地晒着他黝黑的脊背,那背上积了盐霜,亮晶晶地排出一片片古怪的花纹。他时而用脏毛巾抹一把脸,那毛巾上的汗便又添了一层。我每经过,总见他笑呵呵地招呼客人,仿佛全无烦恼。然而有一日,我见他蹲在摊后,捧着个粗瓷碗扒饭,扒着扒着,忽地落下泪来。泪混着汗,滴在饭里,他也浑然不觉,仍旧大口吞咽着。我想,这便是所谓的"放'夏'烦恼"么?
至于“快乐多一点”,更显得可笑。快乐岂是能量产的物事?它来无影去无踪,人愈是追逐,它愈是逃遁得快。况且在这炎威之下,连思绪都被蒸得模糊了,快乐从何而来?前日见一个孩童在烈日下追逐一只断了线的风筝,跑得满头大汗,脸蛋通红,却笑得极欢畅。风筝终于挂在高压电线上,孩童立时哭了起来。他的母亲从屋里冲出,一把拽了他回去,顺手还给了他一记耳光。快乐便是这般脆弱的东西,转瞬即逝。
城里的阔人们自有消夏的法子。他们躲在冷气充足的房间里,啜着冰镇的饮料,谈论文艺与人生。他们的烦恼是精致的,疲惫是高雅的,快乐也是经过精心调配的。他们笔下的夏天总是充满诗意,仿佛那毒日头从不曾晒焦过庄稼,热浪从不曾蒸死过穷人。他们的"放'夏'烦恼",不过是一种消遣罢了。
我老家的一个老农夫,他说最喜欢立夏这个节气。问他缘故,他说立夏后日头长,干活的时间多,庄稼长得快。他说这话时,脸上的皱纹里嵌着去年夏天的尘土。我想,这才是真正与夏相守的人。他的烦恼、疲惫与快乐,都与那土地紧密相连,做不得假,也逃不脱。
立夏之日,我来到工地。工人们正在午休,三三两两地蜷在阴凉处。他们的鼾声与远处的机器声混在一处,竟显出几分和谐来。一个年轻的工人醒了,揉着眼睛,从怀里掏出半个冷馒头啃着。我忽然觉得,或许烦恼与疲惫本就是生活的底色,而快乐不过是偶尔泛起的微光。人们大可不必强求放下什么,追求什么,只要还能在烈日下啃一口冷馒头,生活便自有其坚韧的力量。
夏来了,带着它固有的酷烈与丰沛。人们照例要说些应景的话,做些应景的事。而真正的夏天,永远在话语之外,在那些默默流汗的脊背上,在那些无声忍耐的眼睛里。(杭州余杭:王怀海)
版权声明:本站所发布信息均整理自互联网具有公开性、共享性的信息,发布此信息旨在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,不代表本网站立场,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并注明出处,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,我们将在24小时内更正、删除。投诉举报:admin#chuanshi.cn(#替换成@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