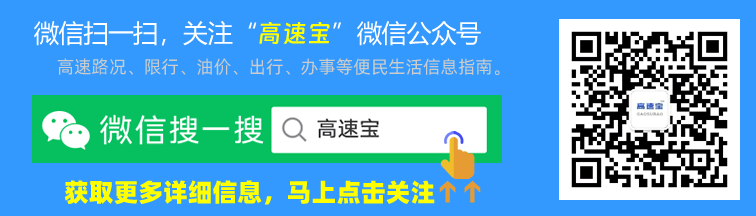不罢休者的黄河
初中校长曾赠我一句评语: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”我深深颔首,这六个字早已刻入骨髓,融进了每一次呼吸吐纳之中。我确实如此,认定的事,哪怕撞上南墙也决不回头,即便滔滔黄河横亘眼前,也照样要寻路泅渡——除非我亲眼看见那赤裸裸的残酷真相,真真切切地触摸到那令人心碎的“讨厌”,才会心甘情愿松手,放下。

林晚,我的名字,但我的心思却从未晚过,反而早早地、固执地停驻在了陈阳身上。陈阳,他周身仿佛裹着一层阳光,明亮得刺眼,笑容像是提前预备好的暖意,熨帖着每个靠近他的人。我悄悄留意他很久了,他不经意间说起喜欢城西老铺子的豆浆油条,我便牢牢记下。从那天起,我风雨无阻,每天清晨都会准时出现在那家铺子前,再将热腾腾的早餐递到他手上。
这一递,便递了整整三年。三年里,我如同完成一道坚不可摧的证明题,日复一日,用恒心求证着某种渺茫的答案。无论是寒冬的霜风割面,还是酷暑的闷热蒸腾,亦或是同学们由初时的惊奇围观渐渐变为窃窃私语、最终归于沉默的注视,都无法动摇我分毫。我像固执的解题人,不眠不休推演着那看似无解的公式,坚信只要步骤足够多、时间足够长,答案终会水落石出。
那天清晨,我照例提着那份温热,脚步轻快地走向陈阳的课桌。教室里空荡荡的,只有值日生扫地的声音。我放下早餐盒,习惯性地朝窗外望去,目光瞬间被钉住了——陈阳和一个明艳的女孩站在楼下,他正低头为她拂去发梢的落叶,动作轻柔得像是触碰一件珍宝。女孩笑靥如花,他眼中流淌的光,是我这三年来从未接收过的暖流。
我的心猛地一沉,但固执的惯性仍在推着我。我匆匆下楼,攥着袋子,脚步慌乱地追了出去,仿佛要把那刺眼的画面从眼前抹掉。转过教学楼拐角,那个熟悉的垃圾桶赫然闯入眼帘。盖子半开,我那精心准备的早餐盒赫然躺在最上面,金黄的油条浸在浑浊的污水里,豆浆泼洒出来,濡湿了旁边揉皱的废纸。盒子的一角,还挂着一片孤零零的菜叶,像是被无情丢弃的昨日残屑。那一刻,我听见内心那座用三年时间垒砌起来的堤坝,轰然溃塌。
我默默走过去,俯身,小心翼翼地把那不堪的盒子从污秽中捡拾出来。指尖沾上了油腻的污迹,那触感冰冷又粘腻,一路渗进心里。我没有再回头看一眼教学楼的方向,只是捧着那只湿漉漉、脏兮兮的盒子,径直走向了水房。水龙头哗哗作响,我一遍遍冲洗着,水流带走污渍,也仿佛冲刷着某种沉重的附着物。洗净的盒子在阳光下泛着清冷的光泽。我把它擦干,仔细地放回了自己的书包深处——如同郑重其事地安放起一具过往的骸骨。
那天的课我听得异常专注,黑板上的公式与定理从未如此清晰。放学的铃声响起,我收拾书包,动作利落。经过陈阳空着的座位时,脚步没有丝毫停顿,像是经过一片无意义的空白。原来,黄河并非总需泅渡,有时,抵达河岸本身就是目的。那浊浪滔天的景象,恰是最清晰的界碑,它告诉我,此岸并非荒芜,那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”的倔强,亦可用来守护自己内心的清冽与完整——有些黄河,渡不过才是慈悲。
从此岸回望,我终于懂得,校长当年那句箴言并非指向外在的征服,而是内在的完整。真正的不罢休,是当撞上那名为“残酷”的界碑时,有勇气将那份焚心蚀骨的执念,最终调转方向,化成了内心深处的自我和解与郑重托付。(杭州余杭:王怀海)
版权声明:本站所发布信息均整理自互联网具有公开性、共享性的信息,发布此信息旨在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,不代表本网站立场,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并注明出处,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,我们将在24小时内更正、删除。投诉举报:admin#chuanshi.cn(#替换成@)